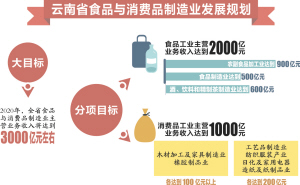摘要:本文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对战略规划复兴的影响。政府对此的反映集中在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之上,从而影响了战略规划的本质目标,本文通过研究伦敦、悉尼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表明这些城市为强化它们“世界城市”的地位而制定战略规划。其中制度安排以及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在这些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在过去20年中有关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考不断增加,但是这种思考仍然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逻辑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使城市吸引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城市规划必须对这种迫切性做出反应。本文通过研究伦敦、悉尼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阐述了这些城市为强化它们“世界城市”(worldcity)的地位,如何制定它们未来的战略。其中制度的安排以及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在这些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引言
本章主要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对战略规划复兴的影响。我认为,经济的转变间接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决策;它们通过不同的方法被解释,激发了权力的网络化,影响了制度的设定,并且在确定的议程中体现出来。政府的反应过多地集中到城市间的竞争上来,这影响了编制城市战略的本质目标。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目前众多城市战略思考的思维框架,吸引外来投资的成功与否成为评价最终规划的主要标准。因此,战略规划越来越像一个与跨国贸易集团进行沟通的文本。
全球化经常被描述为对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产生着影响的新变量,在过去20年中,它“是绝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争端的中心”(Giddens 1998),成为了“1990年代的滥觞”(Stilwell 1997)。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例如,它是否符合真实状况或者它仅仅是一个理想框架?它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能够被控制的?它是否是什么新东西?当然.全球化的一些特定领域是值得关注的(例如Sklair注意到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的蔓延1995)。本文将主要关注经济方面.关注全球化经济不断延伸的触角,并且探索它们与城市规划的联系。在讨论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被转移到了“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过程中.还会涉及到政治领域的一些争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了城市的重要作用。
本文在第一部分,将简要回顾在发达国家主要城市中对于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变化的讨论。这些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对现存的或者预感到的压力做出反应。文章接下来阐述了三个城市的战略规划:伦敦、悉尼和新加坡。伦敦是全球公认的位于全球城市第一等级中的一个“世界城市”;悉尼是一个在城市越来越强调自主的时代仍然在区域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良好范例;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本文中,我着重描述了全球变化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对战略思维的影响,这些影响给城市规划设置了特定的框架。我们可以通过对规划政策更为详细的检讨追溯这种影响的轨迹,但这超出了这篇短文所能覆盖的视野。
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假说
人们发觉,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式已经出现,导致了城市的经济活动开始发生变化。一种以“世界城市”为顶点的全球城市等级结构已经形成,加强竞争力成为政治的主导对策。有一系列的原因相互关联着:新的经济力量已经在全球层面进行操作,这些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城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与民族国家相比越来越有力量。这些都在加强着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规划必须为适应全球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做出反应。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定义,是指经济在技术的支持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网络结构。航空运输系统的改善以及新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造就的“电子空间”使全球范围内的物理移动变得更加简易(Castells 1996)。全球经济互联的特性使这个网络中某个特定的国家碰到问题时,在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都产生波动,例如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或者巴西。观察全球化的另外一个角度是观察公司的行为。顶尖的公司在运作、产品、行政管理、选址和营销方面的决策都淡化了国家的边界,采用一种全球视野。这种观点在商业和管理的研究中表达得非常明显(Ohmea 1995),虽然它被批评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过于强调民族国家的消失趋势(Gray 1998)。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其他的时期都有同样的全球化现象{Knox 1997;Storper 1997;Hirst & Thompson 1996}。这种观点,尽管证明许多全球化的理论实际上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新旧全球化之间的一些本质性差别,它的可信度被大大地削弱了。在全球化的广度和强度上,现代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有着显著不同。另外一种意见反对民族国家正在消亡的观念,当前的实证分析为他们提供了证据。这种批评认为国家力量的退化程度被夸大了,尽管权力和责任已经在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上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国家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同于全球一国家的二元结构,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模式已经出现(Sassenl995;Hobsbawnl998)。这种模式包括新的全球规则和区域结构,例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自主权越来越大的城市。在这种模式中,民族国家仍然扮演着中枢性的中介作用。证据也显示,其实没有几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大多数的国际公司仍然植根于他们的祖国,全球市场并不存在完美的竞争和信息环境。在一个不断进行冒险的环境中,本土优势和文化因素仍然非常重要,例如公司对他们研发活动的选址就局限在非常特定的地点。
尽管有以上的争论,人们仍然认为全球化给城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议题是新的城市等级结构的出现。最早阐述这一点的著述来自于Friedman和Wolff(1982),Friedman将其发展为“世界城市假说”(world city hypothesis)。城市按照它们在全球的角色划分种类,Friedman确定了一些主要的和次要的城市。其他的著述采用了这个(分级的)观点,并且划分了自己的等级结构,例如Thrift(1989)将纽约、伦敦和东京定义为全球城(Global City),第二级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第三级是地区中心城市。这些分类决定于应用什么样的划分标准。Friedman和Thrift特别关注跨国机构、银行和跨国集团总部的集中,因此,这些公司行政决策中心的集中与否被看作全球城的基本衡量标准。这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站在了世界城市等级结构顶端的根本共同点。Sassen在她的主要著作《全球城》(The Global City)中考察了以上三个城市。她在世界城市假说的基础上,对城市的经济活动,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统计进行了详细的实证调查。她文章的中心论点是,这些城市是控制跨国商务和商业行为的命令发布地。由于全球化允许在全球更广泛的范围分布经济功能,因此对中央控制和管理的要求也增加了,这种功能被集中到了更少、更关键的地点上。一些特定的活动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需要也在全球层面上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金融服务产业。这些组织的高度集中衍生了更多的金融、信息产业和传播业的创新性服务或产品。她论著中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对贫富分化的极化特征的描述,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产生了高收入阶层,以及为这个阶层服务的以移民为主的低收入阶层。这种极化会在空间上产生影响,例如“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现象。正如Peter Hall(1998)所说,“对于城市的社会公正和城市均衡所面临的尖锐问题是:富裕的岛屿被贫穷和愤怒的大海所包围,这是城市战略思维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
“世界城市假说”和Sassen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们建立了全球经济运行和城市自身变化之间的确定联系。虽然从这些研究中仍然可以得到许多结论,但是这些可能的结论需要有更复杂的分析过程。这三个城市的不同点被忽略了,例如纽约有更多的移民:在伦敦,国家在消除伦敦的极化影响时扮演了重要角色(Hamnett 1996);位于东京的公司虽然在名义上是跨国公司,但是它们仍然牢牢地根植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三个城市具有的许多特征,诸如金融业和高级服务业的增长,在等级结构中较低层次的城市中也有发生的迹象。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特征到底是现代城市的普遍特征呢,还是仅仅限于这三个城市才有的独特特征。类似的,社会的极化现象也可以说成是普遍的经济变迁带来的趋势,而不是这些城市吸引了核心指令和控制职能后造成的恶果。也有人说这些分析带有决定论的色彩。正如Storper所说,将城市看成一个对外界力量做出反应的机械系统其实限制了解释的说服力(1997)。也许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地区文化和文脉的相对重要性将会显示得更加明显(Dieleman & Hamnett 1994)。
在列举了许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争论以及它对城市的影响之后,我现在来讨论政策的反应。最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假如城市要获得竞争优势,它必须在吸引全球化经济的那些先进领域的投资竞赛中击败其他竞争对手。正如Harvey(1989)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城市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管理城市转向了“企业家”式的(entrepreneurialison)经营。这种企业家式思维的范例包括,将城市作为一种产品进行营销。近年来,把城市形象作为城市营销的重要实点的研究在不断深入(Ashworth & Voogd 1990;Smyth 1994;philo & Kearns 1993;Paddison 1993)。特殊的城市意向和视觉景观可以影响城市政策的倾斜程度,一般说来,重大事件和开发活动总能够吸引媒体的关注。城市营销针对那些特定的、消费“城市“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可能是Friedman和Sassen所界定的跨国集团的决策者,以及其他的决定全球城市地位的人们。这些集团需要的土地、房屋和设施,以及与此有关的活动在城市营销战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设施的供应可能对城市的原住民造成一些问题,例如更高的房价、中产阶级化或者机场的噪音,也包括丧失了为满足“全球城”功能而占用的资源的机会成本。
文章在下面部分将讨论伦敦、悉尼和新加坡在近年完成的战略规划。作者提出的假设是,对全球化的回应造成了一种新的战略观,它直接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这三个城市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置身于竞争的环境中,它们认为必须通过积极的行动把握世界经济运行的脉搏,保持自己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新的城市战略被看作其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紧紧地与城市营销联系在一起。
伦敦:世界城市
由于在1986年取消了大伦敦议会(the Greater London Council)后缺少一个大都市区域的联合政府,伦敦因此成为发展进程中相对的后来者。此后,伦敦33个地方规划管理机构为了讨论区域的规划问题,成立了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拥有来自地方规划机构的代表,负责准备战略规划报告,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它的报告要提交给中央政府,转变为城市的战略规划法定导则才能发挥作用。在那个时代不干涉主义意识形态(the non—interventionist ideology)的影响下,1989年的法定导则只有几页纸:设定了一些地方政府操作的主要参数。作为不干涉主义意识形态和松散的制度体系的产物,在大伦敦议会取消后,只有非常少的战略规划得到了实施。尽管LPAC编制了战略政策,但是对中央政府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要求采取更多统一行动的压力不断增加。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一个包含了金融区的很小的地方政府,由于中世纪赋予商业区的特权拥有独特的制度安排,他们在编制报告和资助有关困难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例如,它委托伦敦商学院研究了在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如何保障伦敦金融服务行业的持续成功(London Business School 1995)。这个研究的结论之一是,伦敦缺少一个统一的声音来提升自己,类似观点在早先的一个咨询报告“伦敦:迈向21世纪的世界城市”中也有所体现(Coopers & Lybrand Deloitte 1991)。这项研究通过对世界顶级商业集团的调查,寻求如何维持伦敦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它由伦敦城、威斯敏斯特城(Westminster)和伦敦码头区开发公司(the London Docklar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资助,LPAC编制。
19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也采纳了这些意见,认为在松散的组织制度结构下,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加强伦敦的竞争地位(Newman & Thornley 1997)。1992年,中央政府组织了“伦敦论坛”(London Forum)来促进首都的发展。但是第二年,这个组织合并到了一个“伦敦优先”(London First)的私人组织中。这造成了此后5年由私人主导伦敦,政府退居二线的战略思维格局。同年,政府宣布:“其他欧洲城市正在为更有效地吸引外来投资进行着积极的重组”(DOE 1993),为此伦敦吸引外资机构“伦敦优先中心”(London First Center)宣布成立。1993年另外一个名为“城市骄傲”(City Pride)的组织成立了。中央政府的意图是,如果它的三个主要城市能够通过提出设想或发展战略说明它们能够在与世界其他城市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政府就返还一部分财政作为支持。三个城市被要求提供一个由公共、私人和志愿的力量合作制定的未来计划书和行动规划。在伦敦,完成这样一个规划的任务被交给了私人组织“伦敦优先”。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过于分散,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城市战略规划中,设置了一个伦敦大臣,一个首都内阁次级委员会(Cabinet Sub-Committee)和伦敦政府办公室(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London)。委员会负责协调内阁各个部门对伦敦发展政策的不同意见,提交了一个力度更大的75页的伦敦战略导则。1995年,还组建了伦敦咨询联合会(the Joint London Advisory Panel),为首都内阁次级委员会提供咨询,这个新的实体由“伦敦优先”组织领导的“伦敦骄傲协作会”(the London Pride Partnerships)的成员组成。这个举措进一步说明了中央政府和私人领域间协作之密切。
1995年,伦敦骄傲计划书公布(the London Pride Prospectus),为伦敦的发展设定了战略框架。在计划书的开篇中,就明确了它的目标是确保伦敦在欧洲唯一的世界城市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标,它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具体任务来对经济造成强大和持续的吸引力,打造世界等级的生产力、巨大的社会凝聚力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生活设施。尽管这个报告中提到了适用性住房、提高空气质量、节约能源和污水管理政策,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报告绝大部分仍着重于经济的增长、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为支撑经济增长和吸引外来投资,报告提出了多种方法,例如提供足够优良的场地、通讯设施、经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市场、推广活动、改善机场道路和更好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个协会的报告通过伦敦咨询联合会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观念,他们的建议在新的、扩充过的战略导则中得以体现(伦敦政府办公室1996a)。在新的导则中,提出“将伦敦提升到世界城市的首都的地位是当前政府的基本政策。为适应竞争,伦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战略规划导则给城市规划一个涵盖发展过程各个方面的框架”。它还警告说,目前伦敦面临来自许多对手的竞争压力,巴黎、法兰克福、巴塞罗那和柏林等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争夺投资和贸易机会”。同年,政府编制了另外一个文件“竞争的首都:加强伦敦竞争力的政府战略”(GOL 1996b),它汇总了政府为达到保证“伦敦在世界城市顶级圈子中的坚定地位”的目标所采用的各种政策。它强化了伦敦发展战略导则的地位,确保地方规划机构能够明确伦敦世界城市的角色,加强对竞争力的重视。
1997年,在保守党政府执政18年后,布莱尔领导的工党赢得大选,英国的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它对伦敦战略规划的制度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全新的政治安排一一大伦敦政府(the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全伦敦选举出来的市长。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整合和协调政策,它将负责编制一个通盘的规划一一“空间发展战略”(the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来协调整个城市的土地使用和城市发展。而作为新政府的辅助单位,伦敦开发部(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则负责编制吸引投资和提高竞争力的经济战略,我们将从中看出这些经济目标是如何同其他战略中的环境和社会目标整合的。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尔在政府需要对全球化进行应对方面持一种消极的态度,他曾经说“既然我们难以想象联合王国从全球市场中单方面退出,那么就必须调整我们的政策来适应它的存在”(Blair 1996)。
悉尼:区域中心
悉尼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澳大利亚的领袖城市(Baum 1997;Stimson 1995)。它是一个国际航空枢纽、重要的金融中心,并且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增长,成为许多希望为东南亚地区服务的跨国公司的落脚点。悉尼都市区战略规划的编制由新南威尔士州承担。1998年,一个自由党和民族党的联盟(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赢得了州的大选,并且按照有限政府的理念组织了政府。削减了州的预算,实行私有化。州政府非常期望将全球的经济活动吸引到悉尼,但是他们发现在基础设施提供和税收优惠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征税的权利把握在联邦政府手中。于是,“州政府持有的土地、城市规划以及开发的权利就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吸引全球投资的主要手段”(Searle & Bounds 1996)。1995年,政府编制了一个名为“为了21世纪的城市”(C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新都市战略.宣告了一种新的战略规划方法的产生,它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并且更具有灵活性。“既然我们进入了一个变化更快速的、全球影响更广泛的时代.都市规划战略也应该更加动态”(Moseley 1995)。新的方法由于缺少分析和过于含糊,受到了地方政府和规划师的批评。
为促成世界城市角色的树立,寻找适宜的商业发展中心地点以吸引Sassen所描述的那些指挥和控制功能的进入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为了21世纪的城市”中所阐述的一个策略就是:“使悉尼成为国内和国际的公司总部、金融和旅游中心,规划管理的发展将帮助悉尼实现这个目标”(规划署1995)。值得注意的是,当悉尼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意见相左时,州政府是如何实现其政策的。州有权介入任何对发展战略有影响的规划决策,Searle(1998)描述了在1980和1990年代州政府是如何在大量的冲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在这个时期,州政府采纳了超前发展的观念,而与此同时,悉尼城市政府的政策完全为当地社团的力量所控制,这造成了对于保留遗产建筑不同态度之间的;中突。州政府利用他们对于大型项目的规划决定权压制了这些反对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这违反了地方规划的规定;还有一些其他机制保证州政府实施自己的决策。在1980年代早期,州政府决定将达令港(Darling Harbor)开发为用单轨交通连接的休闲娱乐中心(Huxley 1991),它必须在1998年之前完工,但是耗时的环境影响评估阻碍了这个计划的推进。因此州议会通过了一个特殊的提案,将规划权下放到新成立的达令港地方规划当局,不必完全遵守议会控制和规划法规的规定(Searle 1998;Daly & Malone 1996)。当专家和社区对建议单轨的反对意见日渐增多时,州政府又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州政府采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是改变悉尼的行政边界,以保证市政府的管辖范围能够紧随这个大都市的发展。1988年州政府指定了一个特殊的中心悉尼规划委员会(Central Sydney Planning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负责准备城市的区域规划,并且决定5007美元以上的建设项目。
1995年工党重新获得了州一级的执政权力,上届政府在“为了21世纪的城市”报告中制定的大部分战略思想符合他们的竞选纲领,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个报告对当前的世界环境研究不够,于是他们发起了另外一个研究,名为“作为全球城的悉尼”(Searle 1996)。在这个研究报告的前言部分,州和区域发展大臣指出:“我们必须确定悉尼的规划有助于增加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率……规划新的、有效的道路和轨道交通网络,支撑现有的就业地点,为它们提供持续的物资供应,这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因素”(Searle 1996)。这个报告非常全面地分析了影响悉尼成为世界城市的因素及其对规划的启示。1997年,州发布了一个新的战略规划回顾——“增长和变革的框架”(Framework for Growth and Change)(Department of Urban Affairs & Planning 1997a)。该报告采纳了许多先前的城市规划建议,增加了促进经济竞争力和灵活性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参照了“作为全球城的悉尼”的研究成果。规划提出建设新的道路、机场和公共交通系统,并且提倡私人部门更多地参与投资。新规划明确了环境质量和全球竞争力之间的联系,但是却忽视了全球化的社会影响。“增长和变革的框架”要求:“州政府继续利用它在大项目上的规划决定权.吸引外来投资,鼓励大公司将区域的总部设置在这个地区”。
1997年8月,在新南威尔士州总督的授权下,一个叫做悉尼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Sydney)的机构建立。它由社区和商业集团的首脑们组成,它的目标是为整个城市在环境,教育、商业投资和艺术方面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个委员会致力于提升悉尼國际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并且试图从中为城市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悉尼委员会1998)。“我们坚信,如果我们试图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个可靠的未来,增加我们在世界和区域中的竞争力,我们就必须更精明地思考、更努力地工作、更好地规划”(悉尼委员会1997)。在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宣言中,表达了对城市规划的重视。“世界上许多主要城市,诸如巴塞罗那、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威尼斯教育我们如何去做。它们给自己的未来描绘了清晰的前景,编制了长期的战略规划来实现这一前景”。这个论断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但是它的目的是明确的。它期望表达的是,悉尼在城市发展的竞争中已经落后了。这个宣言在后面部分表述得更加直接,它不顾上述那些已经编制的战略规划的存在,认为悉尼没有长期战略规划,这表明委员会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更接近于自己想法的规划。因此,他们在1998年聘请了Coopers & Lybrand咨询公司进行“悉尼2020”的战略研究,来“决定要做些什么才能保证和加强悉尼未来是一个全球城”(悉尼委员会1998)。
新加坡:城市国家
新加坡是19世纪作为英国的一个贸易港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1965年独立以前,贸易是新加坡政府最关心的问题。1965年,新的国家从大陆(马来西亚)中独立出来,因而必须寻找生存的战略。尽管新加坡有着良好的国际贸易基础,但无论如何,国家要获得未来的经济安全就必须发展本国的工业,这个国家就是从这一点着手组织他们的经济战略。他们需要建立新的制度结构来吸引、发展和控制一些外国直接投资,例如新加坡银行和提供基础设施的裕廊新城公司。政府为编制战略、吸引潜在投资者的最重要机构是经济发展委员会(EDB: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这显示从最早期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已经致力于提升城市地位的工作。EDB这种干涉主义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期,“为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调整自己,寻找更好的机会和竞争突破点做出了重要贡献”(Cbna 1998)。
土地空间和劳动力市场的狭小,使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他们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领域越来越没有竞争力。EDB认为新加坡应该致力于把新加坡建设成为服务业中心,吸引服务于东南亚地区的大公司总部进入,发展旅游业、银行业和离岸加工业(Chua 1998)。1970年代早期,当政府意识到这里缺乏现代经济的银行服务设施时,就已经提出了需要增加以服务为导向的用地。政府规划了一个名为“金马蹄”(Golden Shoe)的银行和公司区。这个区域融合了旧的商业中心,目前已经容纳了所有的重要公司和政府金融机构。可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是处于规划的悉心指导下的。在最新的战略规划中提出,新加坡的目标是成为全球城。它的优势在于: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悠久传统,在电信产业和机场设施方面的高强度投资,在亚洲经济中的优良地位,拥有安全和洁净的环境,使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
由中央政府编制的经济战略,与城市土地使用和开发规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EDB在另外一个政府机构——城市再开发管委会(URA: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编制的土地使用战略规划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私人力量也被充分吸引到规划编制的过程中,他们积极地将自己的观念灌输给对政府机构决策产生影响的委员会,因此在URA编制规划的过程中就已经采纳了许多咨询委员会。政府机构以及内阁官员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EDB的工作流程发挥了重要作用,URA将各个部门的意见体现到他们编制的全岛战略规划也就是“概念性规划”中的土地使用和开发方面。最近的概念性规划是1991年编制的,其中包含了三个时间阶段,即2000、2010和“X年”。URA的职责是负责“规划和实施新加坡的物质空间发展,建设一个完美的热带城市”(URA 1998)。在以前表述的职责中还包含了“管制”(regulate)这个词汇,但是由于它显得对商务活动不那么友善而被取消了。概念性规划非常明显地具有吸引商务的倾向:“经济发展过去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着眼点,即使新加坡目前已经是一个商业、制造业和金融中心,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点。但是进步不为任何人等候,现在新加坡不能因为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就骄傲自满。如果我们还希望将我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那么动力只能来源于我们的经济”(URA 1991)。规划试图通过“重整城市结构”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必须在今天规划未来经济需要的基础设施,这包括交通和通讯设施、土地和环境质量,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避免中心区域的过度集中。因此新的概念性规划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分散化的政策。它规定4个主要的地区中心各为80万人口服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CBD地区不进行发展。经过对世界其他城市的研究,政府对现有金融街区的扩展进行了规划,新规划借鉴了悉尼和旧金山等中心区滨水城市的经验,围绕着Mariana湾进行开发(Chua 1989),这获益于667公顷的填海工程。这个项目中的一部分作为会展区,其他部分作为CBD的扩展区。无论如何,人们对于城市活力已经有了一定认识,政府采纳了住宅和娱乐设施的混合区划方法。
新规划另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是它对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有了更广泛的认识,注意到高质量的居住设施、优良的环境、娱乐设施和令人兴奋的城市生活等因素产生的影响。因此,规划中提供了更多贴近海滩和休闲设施的滨水低密度住宅区。低密度住宅显然会对短缺的土地资源造成压力,这给规划的另外一个目标——提高环境质量造成了问题。越来越多保留的开敞地区被开发了,这个岛屿唯一保留下来的自然景观区就只剩下了岛中部的水源保护地。环境政策考虑非常多的是“绿色”开发,这成为了新加坡的“美化”运动。规划利用绿带作为居住区的边界,或者配合交通走廊设置绿带,在住宅区内的绿化也受到了重视。大多数的绿化建设是同吸引商业投资联系在一起的,诸如高尔夫球场、休闲娱乐区域和海滩。规划在提供良好的娱乐设施和发掘岛屿的潜力上面花了很大力气。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远期在中心区和机场之间通过填海制造一个新的岛屿,进行休闲设施和高档住宅的开发。最近,规划师期望规划建设一个“24小时的城市”和“咖啡社区”。建设“咖啡社区”的目的是接纳高层次的活动,其实施手段包括在新加坡河两岸开发连续的滨水步道,利用老建筑的价值延长营业时间,发挥历史建筑在晚间的使用价值(Yu-Ningl998)。由于1996年已经放松了对室外餐饮区的严格管制,这个区域成为傍晚时非常热闹的地点(Fongl997)。1998年,URA在城市的中心开辟了新的娱乐区,试图将它提升为“这个城市值得一看的动感娱乐景观”(Brennan 1998)。
讨论
作者在上文中阐述了经济全球化假说导致城市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刺激了战略思考的发展。政府认为,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远景可以改善城市的竞争力和提升城市的品质,这在上述三个城市中都得到了验证。在伦敦,取消伦敦议会(GLC)造成的大都市政府的缺失被各种广泛的组织填补了起来。尽管如此,在1990年代以前,政府仍然面临着来自私人领域的巨大压力,要求制定未来远景规划,促进城市协调发展。大量的研究报告试图说明伦敦是一个世界城市,并且面临着来自欧洲其他大城市持续不断的竞争压力。中央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紧密合作构成了这个时期城市治理的主要形式,这最终促成了同样重视经济竞争重要性的“伦敦战略扩充导则”和“伦敦骄傲计划书”。在悉尼,将城市地位提升到世界城市的重要性已经获得了清楚的共识,州政府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研究提出的建议体现到1995年新编制的大都市战略中。新加坡政府自从国家独立后就扮演了一个积极的干预者的角色,决定城市的发展方向或远景一直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近年,政府工作的中心在于将城市的地位提升到区域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现在开始更加关注娱乐和生活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些提升的目标构成了城市战略规划——概念规划的基础。
在这三个例子中,私人机构对于设定城市未来发展意向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伦敦优先”这个私人机构与政府互通有无,并影响了“伦敦骄傲计划书”的制定;在悉尼,一个类似的机构也对悉尼全球城大战略施加了强大的影响;新加坡政府则利用经济发展委员会来设计战略发展目标,他们从私人领域汲取建议,设定战略规划框架。
上述以全球为导向的三个城市的战略同时将重点设定在商业、会展、休闲和娱乐活动的选址方面,这些用地都被安排在城市中心或具有吸引力的滨水地区。非常有趣的是,制度的设计保障了政治决策能够支持投资进入这些地点。1990年代在伦敦,伦敦城。威斯敏斯特城和政府指定的半官方机构——伦敦码头区开发公司(LDDC),对全伦敦范围内所有编制发展战略的机构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码头区的战略发展地区,LDDC完全取代了民选地方政府的作用。在悉尼,州政府运用自己的权力介入或者是直接操作战略发展。它们为达令港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可以不受现行法律约束的特殊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架空议会,自行其事。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拥有单一的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可以透过低层次的决策机构,编制一个持续的、庞大的CBD扩展规划,直接发挥自己综合和积极的作用。这种设置有助于新加坡推行一个长期的、协调的实施手段,树立外来投资者对于新加坡未来成为世界城市的信心。
在1990年代,这三个城市都重新编制了发展战略,这些战略都根植于城市竞争的讨论,非常坚定地相信城市战略对于促进城市发展的作用。所有的战略都将主要目标设定为吸引外来投资,这反映出私人机构影响的扩大。在所有的案例中,为了协调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特别的制度和方案设计。比城市更高层次的政府掌握了对战略的控制权,并且还设计了许多机制以保证上一级政府的控制意图能够直接贯彻到重要的发展项目中,这些设计保障了经济发展走向不会因地方社团的反对而走样。这些制度的设定并不像许多文献所描述的国家一州/城市的二分法那么简单。在中央、州政府与城市政府之间,政府、社区和为实现发展设置的特殊机构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互动方式。尽管如此,在所有的案例中,对都市发展战略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来都自于上一级的政府和私人团体。
在关于全球化的文献中,对于全球化的过程是否是难以回避的这个问题有许多争论。但是一个事实是,全球经济力量要求城市提供灵活的战略,以便城市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吸引新经济投资,这导致一种融合了许多特定的规划、政策和土地划分的城市战略的诞生。与此同时,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仍然拥有自主权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并且提出自己更广泛的目标体系。这可能包含对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重视。事实表明,在城市不顾一切赢得经济竞争的时候,会给城市带来许多问题,诸如环境退化和社会极化。从长远看,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提示我们应当编制更为综合的战略规划。但是,通过对三个城市的调查,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观念,从中获益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议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本文标签:
| |
|
| 【分享】 【打印】 【收藏】 【关闭】 | |
 |
- 相关内容
- 更多
- 兰州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出炉 [2016-11-4 16:49:33]
- 德州中心城区商业网点规划 三个圈层三大体系 [2015-3-5 15:04:56]
- 印发《南昌市2013-2020年商业网点规划》的通 [2015-3-5 14:48:42]
- 新加坡城市商业中心的规划布局与启示 [2014-12-26 10:49:18]
- 《南阳市中心城区商业网点规划》通过专家评 [2014-11-7 9:17:18]
- 平顶山市新城区商业网点规划通过评审 [2014-7-11 9:28:01]
- 图片资讯
- 更多